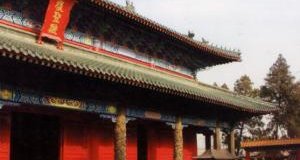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道学家陆王一派 ,假定人本有完全的良知,假定“满街都是圣人”,故以为人只须顺其良知而行,即万不致误。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我知之甚少,不清楚这两位思想家假定“性本善”的依据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满街都是圣人”是缺乏客观性的。普通人和圣人的欲求必定是有差异的,况且什么是“良知”这点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的定义也是不尽相同的。隐约觉得陆王心血可能与释禅之道有所联系,此点需要待以后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后再做深入分析和评判。冯氏继续讲到,孔子初无此意。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本不必即可顺之而行而无不通(此句比较绕口,我理解为人之真性情流露,并不是顺之就能行得通的)。故孔子重视“克己复礼为仁”。然礼犹外部之规范。除此外部规范外,吾人内部尚且有可为行为之标准者。若“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吾人之性情之流露,自合乎适当的分际。故“直”尚有行不通处,而“仁”则无行不通处。故仁为孔子“一贯”之道,中心之学说。我在想“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始思想动机是什么,因为从冯氏的观点来看,更像是为了“行得通”。那么“行得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有自私自利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如果仅停止在能“无行不通处”的层面,而不去想上面的问题,那就可能只重视了外在的形式,而忽略或放弃了其本质。我和冯先生在此观点有所分歧,我认为孔子提倡行“仁”,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激发人们进一步去了解和探索宇宙的真谛。天下之事,从无某种定论可以行通或行不通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并且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发展上上世纪,还不是被西洋的坚船利炮给轰开了国门。当然这里面有无数的其他历史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日趋保守和个人功利的儒家思想是最主要的几个原因之一。
,假定人本有完全的良知,假定“满街都是圣人”,故以为人只须顺其良知而行,即万不致误。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我知之甚少,不清楚这两位思想家假定“性本善”的依据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满街都是圣人”是缺乏客观性的。普通人和圣人的欲求必定是有差异的,况且什么是“良知”这点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的定义也是不尽相同的。隐约觉得陆王心血可能与释禅之道有所联系,此点需要待以后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后再做深入分析和评判。冯氏继续讲到,孔子初无此意。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本不必即可顺之而行而无不通(此句比较绕口,我理解为人之真性情流露,并不是顺之就能行得通的)。故孔子重视“克己复礼为仁”。然礼犹外部之规范。除此外部规范外,吾人内部尚且有可为行为之标准者。若“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吾人之性情之流露,自合乎适当的分际。故“直”尚有行不通处,而“仁”则无行不通处。故仁为孔子“一贯”之道,中心之学说。我在想“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始思想动机是什么,因为从冯氏的观点来看,更像是为了“行得通”。那么“行得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有自私自利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如果仅停止在能“无行不通处”的层面,而不去想上面的问题,那就可能只重视了外在的形式,而忽略或放弃了其本质。我和冯先生在此观点有所分歧,我认为孔子提倡行“仁”,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激发人们进一步去了解和探索宇宙的真谛。天下之事,从无某种定论可以行通或行不通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并且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发展上上世纪,还不是被西洋的坚船利炮给轰开了国门。当然这里面有无数的其他历史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日趋保守和个人功利的儒家思想是最主要的几个原因之一。
孔子认为仁为人之全德的代名词。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从宋辽金时代开始,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一位皇帝的庙号为“仁宗”。宋朝有宋仁宗,辽国有辽仁宗,西夏有夏仁宗,元朝有元仁宗,明朝有明仁宗,清朝有清仁宗,除了金朝没有此庙号,而金朝皇帝的谥号中是多带仁字的。宋仁宗是首位得此殊荣者,其后才有辽仁宗和夏仁宗。其原因我想大致如下,北宋开国后不久,理学蓬勃发展,其思想慢慢影响到邻国,甚至可能推动了辽金夏的进一步汉化,所以辽夏两国也认为“仁”是最高的赞誉之一。那么究竟需要什么资格,才能称做“仁”呢?先假定排除臣子们拍马屁的可能性,能得到“仁”的庙号的皇帝或国君通常是在位期间基本无大战事,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修养的。这两点说起来简单,可是要真的能做到,靠的不仅仅是皇帝个人的能力,还要看看历史给予他的运气了。
“为仁之方”在于“能近取譬” ,即谓为仁之方法在于推己以及人也。“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也。“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也。实行忠恕即实行仁。这里是隐藏着一个问题:人之所欲是否相同?答案肯定是不确定的,在某种条件下成立,在某种条件下不成立。假设有位商人企图向海瑞海青天行贿,商人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海大人是那种宁死也绝不收取账款的人。商人求的是利,而海大人则求的是正理名教,他们的欲望明显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里的“欲”大多是私欲,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对事情发展的预测起到参考作用,同时也有可能将一己之阴暗不可告人的“私欲”扩散开来,甚至也有可能对他人的思想造成禁锢。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成语故事,有位渔民冬天在湖里打鱼,由于身体长时间处于运动状态所以觉得有点热,就脱掉了外衣。这时,他想既然这么热,船仓里的小宝宝肯定也会觉得热,于是进去帮小宝宝脱掉了外套。又过了一会,他干得满头大汗,索性连内衣也脱了,同样他也帮小宝宝把内衣脱了。等他做完手工的工作回到船舱休息时,发现小宝宝都快冻僵了。可见,“己之欲”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决策和行动的首要因素。孔子肯定知道这点,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里要看看他说的主语。孔子说的是诸如尧舜之类的圣人,而圣人是通宵世间万物的,所以他们“必定”推知“人之欲”。此言经后世流传,人们往往忘记了原有的主语,而把自己或别人放在此主语位置上,无视自己和圣人之境的差别,所以得到的结果也是与孔子此言相差较大的。同样对于后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此理。如果“不欲”后面是社会观点中普遍认为的“坏事”,比如犯罪,那么这句话是可以说的通的;如果后面是“好事”,比如见义勇为,拾金不昧,仗义执言呢?那么这句话就有些消极了。当然,圣人们从来都是做好事,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怎么做都是行得通的。而对于普通人,只能将此作为参考,不能因其妄做决策了。
,即谓为仁之方法在于推己以及人也。“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也。“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也。实行忠恕即实行仁。这里是隐藏着一个问题:人之所欲是否相同?答案肯定是不确定的,在某种条件下成立,在某种条件下不成立。假设有位商人企图向海瑞海青天行贿,商人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海大人是那种宁死也绝不收取账款的人。商人求的是利,而海大人则求的是正理名教,他们的欲望明显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里的“欲”大多是私欲,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对事情发展的预测起到参考作用,同时也有可能将一己之阴暗不可告人的“私欲”扩散开来,甚至也有可能对他人的思想造成禁锢。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成语故事,有位渔民冬天在湖里打鱼,由于身体长时间处于运动状态所以觉得有点热,就脱掉了外衣。这时,他想既然这么热,船仓里的小宝宝肯定也会觉得热,于是进去帮小宝宝脱掉了外套。又过了一会,他干得满头大汗,索性连内衣也脱了,同样他也帮小宝宝把内衣脱了。等他做完手工的工作回到船舱休息时,发现小宝宝都快冻僵了。可见,“己之欲”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决策和行动的首要因素。孔子肯定知道这点,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里要看看他说的主语。孔子说的是诸如尧舜之类的圣人,而圣人是通宵世间万物的,所以他们“必定”推知“人之欲”。此言经后世流传,人们往往忘记了原有的主语,而把自己或别人放在此主语位置上,无视自己和圣人之境的差别,所以得到的结果也是与孔子此言相差较大的。同样对于后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此理。如果“不欲”后面是社会观点中普遍认为的“坏事”,比如犯罪,那么这句话是可以说的通的;如果后面是“好事”,比如见义勇为,拾金不昧,仗义执言呢?那么这句话就有些消极了。当然,圣人们从来都是做好事,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怎么做都是行得通的。而对于普通人,只能将此作为参考,不能因其妄做决策了。
刚才在找本篇标题图片时,看到网上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解释为自己不想别人用什么方式对自己,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去对别人。我不太认同这种带有西方生活哲学的解释。孔子这番话是对子贡问仁的回复,将”不欲”理解为不想去做的事情,不要别人去做。在当年社会化分工极为细致的情况下,有的人恰恰是依赖于另一部分人“不欲”去生活的。有人可能说,我之所不欲,并没有强加给他们呀,我并不需要为他们承担什么责任,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可是,这种“不欲”也是一种人为的欲望。选择的真正起点应该是“欲”和“不欲”的首次区分。而区分的标准,往往是脱离了社会道德标准的,一念之间所形成的。这个问题我还得好好想想。
《论语.雍也》有云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四书集注》有云,博,广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圣以地言,则造其极之名也(此处的意思我理解为某个时期在某地理区域取得很好政绩的人,即圣人)。乎者,疑而未定之辞。病,心有所不定也。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则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难愈远矣。(子贡的假设中标准要求极高,即使是古代的圣人也无法达到。从子贡的问题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心怀大志的人。有志向当然是好事情。如果实现目标极其困难,那么通常也会很难找到适合个人情况的方式去达到该目标的。甚至可能出现志向高远,人也非常勤奋努力,可是总想是在原地打转,进展极小。孔子及时提醒子贡,同时给出了现实生活中可行的为仁的方法)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四书集注》有云,博,广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圣以地言,则造其极之名也(此处的意思我理解为某个时期在某地理区域取得很好政绩的人,即圣人)。乎者,疑而未定之辞。病,心有所不定也。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则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难愈远矣。(子贡的假设中标准要求极高,即使是古代的圣人也无法达到。从子贡的问题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心怀大志的人。有志向当然是好事情。如果实现目标极其困难,那么通常也会很难找到适合个人情况的方式去达到该目标的。甚至可能出现志向高远,人也非常勤奋努力,可是总想是在原地打转,进展极小。孔子及时提醒子贡,同时给出了现实生活中可行的为仁的方法)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又曰:“《论语》言‘尧、舜其犹病诸’者二。夫博施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有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朱子曰:‘五十始衰,非帛不暖;非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饱,非七十不得食也。’可见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是社会的极理想模式)。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顾其养有所不赡而。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济众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治不过九州。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顾其治有所不及尔。此病济之不众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则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博施广济是永无止境,一旦认为自己做得很好,那么就和广博相悖了)”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人,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虽怀大志,亦需从基础的修身功夫做起)”吕氏,可能是吕公著。据说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皇帝问谁是中原品学兼优之士,欧阳修首推吕公著。
冯氏认为,仁为人之性情之真的 ,而又须为合礼的流露也。《论语.颜渊》又云,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四书集注》的注释如下。敬以持己,怨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内外无怨,亦以其效言之,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旋中礼。唯谨独,便是守之之法。”或问:“出门使民之时,如此可也;未出门、使民之时,如之何?”曰:“此俨若思时也,有诸中而后见于外。观其出门、使民之时,其敬如此,则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门、使民然后有此敬也。”朱子曰:“愚按,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然学者诚能从事于敬恕之间而有德焉,亦将无己之可克矣。”乾,天,男子;坤,地,女子。孔子教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教冉有“出门使民”之事。虽是因材施教,但是朱子亦认为颜渊的学问层次是高于冉有的。我的看法是,孔子在《雍也》篇开头提到的“雍也可以使南面”,言冉雍有人君之度,可见孔子是很欣赏这位学生的。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孔子对颜渊和冉雍的回复不同?可能的原因是,颜渊是学院型的,冉雍是社会应用型的。不能说学院派就高于社会派,这是傲慢和狭隘的。朱子有此想法,可能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有崇尚脑力劳动鄙视体力劳动,延伸至学院派为乾而社会应用型为坤之观点。程子之言,乃是告诫“君子慎独”:外在的出门使民做得再好,如果不为人知的想法和行为是虚伪自私的,那么也不是真正的仁。孔子此言亦有“制之于外,以安其内”之意。“制于外”目的还是“安其内”,所以不能流于外在形势,而要通过“外”去探索内在的实质。
,而又须为合礼的流露也。《论语.颜渊》又云,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四书集注》的注释如下。敬以持己,怨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内外无怨,亦以其效言之,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旋中礼。唯谨独,便是守之之法。”或问:“出门使民之时,如此可也;未出门、使民之时,如之何?”曰:“此俨若思时也,有诸中而后见于外。观其出门、使民之时,其敬如此,则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门、使民然后有此敬也。”朱子曰:“愚按,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然学者诚能从事于敬恕之间而有德焉,亦将无己之可克矣。”乾,天,男子;坤,地,女子。孔子教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教冉有“出门使民”之事。虽是因材施教,但是朱子亦认为颜渊的学问层次是高于冉有的。我的看法是,孔子在《雍也》篇开头提到的“雍也可以使南面”,言冉雍有人君之度,可见孔子是很欣赏这位学生的。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孔子对颜渊和冉雍的回复不同?可能的原因是,颜渊是学院型的,冉雍是社会应用型的。不能说学院派就高于社会派,这是傲慢和狭隘的。朱子有此想法,可能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有崇尚脑力劳动鄙视体力劳动,延伸至学院派为乾而社会应用型为坤之观点。程子之言,乃是告诫“君子慎独”:外在的出门使民做得再好,如果不为人知的想法和行为是虚伪自私的,那么也不是真正的仁。孔子此言亦有“制之于外,以安其内”之意。“制于外”目的还是“安其内”,所以不能流于外在形势,而要通过“外”去探索内在的实质。
《论语.颜渊》有云,颜渊问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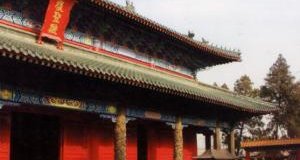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四书集注》的注释如下。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我认为此处的反通返)。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朱子认为人所之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与我矣。(朱子也认为私欲是不可完全战胜的,但是如果不能时常胜私欲,那么是永远无法接近全德的;明代狂儒李贽反对程朱之说,认为私欲是自然存在的,人有了私欲,社会才会不断进步。我认为可能后者的说法有一个潜藏的前提条件,即人们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道德准则;而朱子所担心的就是私欲过度,会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这个“度”极其不好把握呀。能克之,则需时常克之,严守清规戒律,少了很多生活的乐趣,社会也缺乏自然的推陈出新而进步;不能克之,则欲壑难平,人容易放纵自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科学的创新和进步,但是更容易出现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公共价值观的沦丧,导致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批评王阳明李卓吾等人危害社会的理由可能也在于此吧。我认为中间必有一个平衡的区间,如果如传统儒生所言整天克己,那么这种“难”是容易的选择,因为它无视了人的主观欲望;而李贽等提出的则是难度更高的要求。不能因为容易就说它是正确的方向,也不能因为困难就认为它全无道理。两者之间是有互相妥协的区间的。如果定义这个区间,需要在不同时代认真去探索和研究)。归,犹与也。又言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此句让我想到了晚清名人曾国藩,他每日坚持做笔记,三省其身,做的就是“克”的作业;突然我又想,若人真的克尽私欲,岂非社会上缺乏人情?缺乏人情味的人会给人古板僵化的印象,这应该不是真正的仁的境界吧。有待思考)。程子曰:“非礼处即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德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谢氏曰:“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四书集注》的注释如下。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我认为此处的反通返)。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朱子认为人所之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与我矣。(朱子也认为私欲是不可完全战胜的,但是如果不能时常胜私欲,那么是永远无法接近全德的;明代狂儒李贽反对程朱之说,认为私欲是自然存在的,人有了私欲,社会才会不断进步。我认为可能后者的说法有一个潜藏的前提条件,即人们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道德准则;而朱子所担心的就是私欲过度,会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这个“度”极其不好把握呀。能克之,则需时常克之,严守清规戒律,少了很多生活的乐趣,社会也缺乏自然的推陈出新而进步;不能克之,则欲壑难平,人容易放纵自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科学的创新和进步,但是更容易出现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公共价值观的沦丧,导致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批评王阳明李卓吾等人危害社会的理由可能也在于此吧。我认为中间必有一个平衡的区间,如果如传统儒生所言整天克己,那么这种“难”是容易的选择,因为它无视了人的主观欲望;而李贽等提出的则是难度更高的要求。不能因为容易就说它是正确的方向,也不能因为困难就认为它全无道理。两者之间是有互相妥协的区间的。如果定义这个区间,需要在不同时代认真去探索和研究)。归,犹与也。又言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此句让我想到了晚清名人曾国藩,他每日坚持做笔记,三省其身,做的就是“克”的作业;突然我又想,若人真的克尽私欲,岂非社会上缺乏人情?缺乏人情味的人会给人古板僵化的印象,这应该不是真正的仁的境界吧。有待思考)。程子曰:“非礼处即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德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谢氏曰:“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
目,条件也。颜渊闻夫子之言,则于天理人欲之际,已判然矣,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请其条目也。非礼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辞。是人心之所以为主,而胜私复礼之机也。胜私,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请事斯语”,颜子默识其礼,又自知其力有以胜之,故直以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事斯语(事事都是这以这样的准则来做的),所以进于圣人。后置学圣人者,宜服膺(膺,音鹰,意胸。服膺,铭记于心)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视箴》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其《听箴》曰:‘人有乘彝(彝,常理,法理),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其《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宜。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音审,况且)是枢机,兴戎(兴戎,发起战争,引起争端)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虚妄,放荡),伤烦则支。己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其《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愚(朱子)按,此章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几,非至健不能致其决。故惟颜子得闻之,而凡学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发明亲切,学者尤宜深玩。”
《论语.里仁》首句为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晦翁先生注曰:“知,去声。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焉,则失其是否只本心,而不得为知矣。”我认为“知”可能通“智”。从字面上看词句有两种解释。一,如果不选择与仁者相邻而居,那么是不明智的;二,如果知道有仁厚之俗的地方是好的居处,而且选择了在此处生活,但是自己于当地民风相悖,不行“仁厚”之事,那么是无法领会真正的仁之”美“的。我比较倾向于后者。人如果只慕名里仁为美,可是并不知道为何为美,不知道在里仁的环境中该如何行仁,这和“仁”是违背的,是沽名钓誉的伪智行为。《里仁第四》中,孔子又云:“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冯氏曰:“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或有所偏而为过,然要之为性情之真的流露,故观过斯知仁矣。”党,类也。程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类。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尹氏曰:“由此观之,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尹氏,尹焞。焞,因吞,光明之意,焞耀天地。程颐的弟子)吴氏曰:“后汉吴祐(音又)谓‘掾(音元)以亲故,受汙(汙,通污)辱之名,所谓观过知仁’是也。”朱子曰:“愚按,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谓必俟其有过(俟,因四。等待之意。看来“伺机”原来是错误写法),而后贤否可知也。”朱子此言极为重要,颇有拨乱反正之意。如果世人皆认为只有待其犯错,才知道其贤与不贤,仁与不仁,那就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较为恰当的做法是,观察其人之前或现在的过失,从而判断他在德行方面的厚薄。带有试探性有意为之的“怒之以观其节”,正是朱子认为不可取的。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晦翁先生注曰:“知,去声。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焉,则失其是否只本心,而不得为知矣。”我认为“知”可能通“智”。从字面上看词句有两种解释。一,如果不选择与仁者相邻而居,那么是不明智的;二,如果知道有仁厚之俗的地方是好的居处,而且选择了在此处生活,但是自己于当地民风相悖,不行“仁厚”之事,那么是无法领会真正的仁之”美“的。我比较倾向于后者。人如果只慕名里仁为美,可是并不知道为何为美,不知道在里仁的环境中该如何行仁,这和“仁”是违背的,是沽名钓誉的伪智行为。《里仁第四》中,孔子又云:“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冯氏曰:“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或有所偏而为过,然要之为性情之真的流露,故观过斯知仁矣。”党,类也。程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类。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尹氏曰:“由此观之,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尹氏,尹焞。焞,因吞,光明之意,焞耀天地。程颐的弟子)吴氏曰:“后汉吴祐(音又)谓‘掾(音元)以亲故,受汙(汙,通污)辱之名,所谓观过知仁’是也。”朱子曰:“愚按,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谓必俟其有过(俟,因四。等待之意。看来“伺机”原来是错误写法),而后贤否可知也。”朱子此言极为重要,颇有拨乱反正之意。如果世人皆认为只有待其犯错,才知道其贤与不贤,仁与不仁,那就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较为恰当的做法是,观察其人之前或现在的过失,从而判断他在德行方面的厚薄。带有试探性有意为之的“怒之以观其节”,正是朱子认为不可取的。
刚才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后汉时期的吴祐是个有趣的人。摘抄相关历史如下。吴祐,字季英,东汉时陈留长桓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今大人逾越五领,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戚所望。此书若诚,择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苡,音以。薏苡,植物名,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供食用,酿酒,并入药。《后汉书.马援传》:初,援在交阯(交阯,今越南东京,汉武帝六年始平南越国),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慾(慾通欲),以胜瘴气。)王阳以衣囊徼名(徼,音较,通侥。求)(王吉,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人。相传王吉为官十分清廉。他在长安居住时,邻家枣树的枝叶伸入其院中,王吉的妻子随意摘了几枚枣子给他吃。事后,王吉得知枣子是偷摘邻家的,便将妻子赶走。邻家听说后,执意要把枣树砍掉,后经再三劝说,王吉才将妻子招回。因此当时流传‘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的佳话。王吉辞官回家时只带自己的行装,毫无积蓄。回乡后衣食亦如同平民百姓。王吉与贡禹情意相投,交往至深,后又‘王阳在位,贡公弹观’的成语)。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恢及止,抚其首曰:“吴氏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丧父,居无檐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豕,音使。猪)于长坦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被父亲的故友羞辱)祐辞谢而已,守志如初。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祐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简,以身率物。民有争讼者,辄闭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闾,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原指里巷的大门,后指人聚居处),重相和解。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欺。啬夫孙性私贼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伏罪。性渐惧,诣阁持衣自首。祐屏左右问其故,性具谈父言。祐曰:“掾以亲故,受污秽之名,所谓观过斯知人矣。”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长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胶东得之。祐呼长谓曰:“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小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长以械自系,曰:“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祐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啮(啮,音聂)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古代诸人,性格竟如此刚烈!
冯友兰先生认为 ,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理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及人者也。《论语.学而》云:“巧言令色,鲜矣仁。”紫阳先生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肆,放纵,任意行事。对于这句话,我颇有感受。“演多了也就是了”,最后会演变成为大众剧本中所要求的角色,而忘却自己本来的理想;“能言会道”,这是褒义的表扬还是贬义的赞美呢?我觉得能言会道,都会有言不由衷或有偏向性意见的时候,否则听众不会买账;既然不买账,那就不是“能”和“会”了。久而久之,能言会道极有可能偏离原先的目标,转而去刻意取悦于人。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持日益膨胀的虚荣心。一旦变得不择手段,人就变得虚伪和冷漠。我认为能做到取悦于人,在某些情形下也不全是坏事和必须“深戒”的;而这种能言会道,能取悦别人的能力,如果能行“仁”,那么将会取得更大的自我成就。《论语.子路》有云:“刚毅木讷(讷,音哪,哪吒的哪同音,语言迟钝)近仁。”巧言令色矫饰以媚悦人,非性情之真的流露,故“鲜矣仁”。“刚毅木讷”之人,质朴有真性情,故“近仁”也。程子曰:“木者,质朴。讷者,迟钝。四者质之近乎仁者也。”杨氏曰:“刚毅则不屈于物欲,木讷则不至于外弛,故近仁。”《论语.颜渊》有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以同情心为本,故爱人为仁也。
,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理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及人者也。《论语.学而》云:“巧言令色,鲜矣仁。”紫阳先生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肆,放纵,任意行事。对于这句话,我颇有感受。“演多了也就是了”,最后会演变成为大众剧本中所要求的角色,而忘却自己本来的理想;“能言会道”,这是褒义的表扬还是贬义的赞美呢?我觉得能言会道,都会有言不由衷或有偏向性意见的时候,否则听众不会买账;既然不买账,那就不是“能”和“会”了。久而久之,能言会道极有可能偏离原先的目标,转而去刻意取悦于人。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持日益膨胀的虚荣心。一旦变得不择手段,人就变得虚伪和冷漠。我认为能做到取悦于人,在某些情形下也不全是坏事和必须“深戒”的;而这种能言会道,能取悦别人的能力,如果能行“仁”,那么将会取得更大的自我成就。《论语.子路》有云:“刚毅木讷(讷,音哪,哪吒的哪同音,语言迟钝)近仁。”巧言令色矫饰以媚悦人,非性情之真的流露,故“鲜矣仁”。“刚毅木讷”之人,质朴有真性情,故“近仁”也。程子曰:“木者,质朴。讷者,迟钝。四者质之近乎仁者也。”杨氏曰:“刚毅则不屈于物欲,木讷则不至于外弛,故近仁。”《论语.颜渊》有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以同情心为本,故爱人为仁也。
《论语.宪问》名自该章第一句“宪问耻”。原宪,字子思,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子贡在卫国为相时,曾去拜放子思。子思对这位同门的能言善辩和会赚钱(后世尊端木赐即子贡为财神)著称的师兄弟说了一段有趣的话“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颇有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论语.宪问》有云,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朱子曰:“此亦原宪以其所能而问也。克,好胜。伐,自矜。怨,忿恨。欲,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谓难矣。仁则天理浑然,自无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程子曰:“人而无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难能也,谓之仁则未也。此圣人开示之深,惜乎宪之不能再问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为仁矣。然亦岂非所谓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复乎礼,则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则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潜藏隐伏于胸中也。岂克己求仁之谓哉?学者察于二者之间,则其所以求仁之功,益亲切而无渗漏矣。”后世明朝的心学代表人物李贽即是批评程朱这种“灭人性,存天理”的观点。《论语补疏》中焦循曰:“孟子称公刘好货,太王好色,与百姓同之,使有积仓而无怨旷。孟子之学,全得诸孔子。此即己达达人,己立立人之义。必屏妃妾,减服食,而于百姓之饥寒仳(音辟)离,漠不关心,则坚瓠(瓠,音户)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絜(通洁)身之士,孔子所不取。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不难,而仁已至矣。绝己之欲则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为仁矣。”
《论语.阳货》又曰:“好直不好学 ,其弊也绞。”冯友兰先生认为,学即学礼也。古时所谓礼之义极广,除现在礼字所有之意义外,古时所谓礼,兼指一切风俗习惯,政治社会制度。子产曰:“夫礼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庄子.天下篇》谓:“礼以道行。”盖凡关于人之行为之规范,皆所谓礼也。孔子为周礼之拥护者,故其教育弟子,除教以知识外,并以礼约束之。颜渊所谓“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是也。惟孔子同时又注重“礼之本”,故又言直。言直则注重个人性情之自由,言礼则注重社会规范对于个人之制裁。前者为孔子之新意,后者乃古代之成规。孔子理想中之“君子”,为能以真性情行礼者,故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四书集注》朱子曰:“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言学者当损有馀,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而杨时的发言更为有趣。杨子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升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通彩)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妙在“宁野”二字。与其造作虚伪,还不如直接把想法说出来。质胜文,人家还可以大致知道要表达的“质”,虽然觉得表达方式鄙略,总算还有可取之处;文胜质,人家根本就不明白要表述的“质”为何物,或受到误导,这种做法好比“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实为作恶了。杨时为程颐,程颢的学生,信奉由诚证心。上述言论即可对此思想管窥一斑。
,其弊也绞。”冯友兰先生认为,学即学礼也。古时所谓礼之义极广,除现在礼字所有之意义外,古时所谓礼,兼指一切风俗习惯,政治社会制度。子产曰:“夫礼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庄子.天下篇》谓:“礼以道行。”盖凡关于人之行为之规范,皆所谓礼也。孔子为周礼之拥护者,故其教育弟子,除教以知识外,并以礼约束之。颜渊所谓“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是也。惟孔子同时又注重“礼之本”,故又言直。言直则注重个人性情之自由,言礼则注重社会规范对于个人之制裁。前者为孔子之新意,后者乃古代之成规。孔子理想中之“君子”,为能以真性情行礼者,故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四书集注》朱子曰:“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言学者当损有馀,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而杨时的发言更为有趣。杨子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升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通彩)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妙在“宁野”二字。与其造作虚伪,还不如直接把想法说出来。质胜文,人家还可以大致知道要表达的“质”,虽然觉得表达方式鄙略,总算还有可取之处;文胜质,人家根本就不明白要表述的“质”为何物,或受到误导,这种做法好比“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实为作恶了。杨时为程颐,程颢的学生,信奉由诚证心。上述言论即可对此思想管窥一斑。
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四书集注》解释为,“行,道也。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馀。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看来圣人也看好不安分的学生,认为老实的学生未必能有所成。孟子曰:“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也。其志嘐嘐然(嘐,音交,志大言大的样子),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琴牢,姓琴名牢,字子张,又字琴张,卫国人,相传为孔子的学生。曾点,字子皙,曾参的父亲,是孔子的早期弟子。在《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侍坐》一文中,孔子让个人言志,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皆有抱负,而曾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音姨,沂河,源自山东,从江苏入海),风乎舞雩(音于,古时求雨的祭祀),咏而归。”孔子表扬说:“吾与点也。”牧皮,相传为孔子弟子。要找到真正满足“文质彬彬”的学生,恐怕是极难的事情。更多的是“质胜文”或“文胜质”的类型,孔子也认为“质胜文”的狂生是首选,“文胜质”的狷生是次选。而没有自己见地和思想的“谨厚”之人,在孔子心中的排名是最末的。由此隐约感到,儒家的思想本质,实有较大的自振创新成份。反过来想,如果都是一帮碌碌无为,毫无自己看法的学生,相比孔子的思想也传不了多久即会消亡;正是因为有了一群性格各异,有明显或潜在“自振”之心的学生,才使得儒家思想充满了生机并在后面蓬勃发展。另外,孔子的这种观点,是否对现在僵化的教育体制有着某种启发呢?
《论语.阳货》有云:“乡原,德之贼也。”原通愿。朱子曰:“乡者,鄙俗之意。乡愿,乡人之愿者。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冯氏曰:“文质彬彬,即中行也。狂狷之行为,虽不合中行,要皆真性情之流露,故亦可取。鄙俗之人同流合污以媚于世,为伪君子,尤劣于真小人矣。”
直虽可贵,尚须“礼以行之” 。《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葸,音洗。畏惧貌),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偷,朱紫阳注释为薄也)。”朱子曰:“绞,急切也。无礼则无节文,故有四者之弊。”我觉得这个“绞”字用得好,所谓“欲速则不达”即如此。另外“笃于亲”的“亲”,我认为做《大学》开篇中“亲民”之“新”,意为君子之责任。张子曰:“人道知所先后,则恭不劳,慎不葸,勇不乱,直不绞,民化而德厚矣。”张子,名张载,北宋年间著名理学家,字横渠,关学的开创者,北宋五子之一(其余四人为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后朱熹在此名单上加上司马光,成为道学六先生)。张横渠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认为读书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代表作是《正蒙》。现今社会有很多人喜欢自诩为“直”,口头禅中总有一句“我这个人很直的”,然后不顾场合地点“畅所欲言”,只管自己说得是否过瘾,没有考虑他人的感受或接受程度。我比较认同范祖禹对礼的定义“事有其序谓之礼”,“事有其序”这句话包含了“有”和“序”。先得存在“序”,才能被“有”。“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是表现形式不同的,但是“序”有隐含包括着对象的存在,只有两者或两者以上的对象才能存在“序”,也只有它们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才能形成“序”,那么怎样才能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稳定呢?关系取决于两者之间的作用力和接口(受力点)。作用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这和现实万物之间的关系是相符的;但是发力点和受力点组成的接口,必须关注其发送和接受,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两者关系的稳定。力是“直”接存在的,而“接口”则定义了它的作用范围。这个“接口”也就是“礼”,众多的接口形成了一个系统,即广义的“礼仪”规范。假设直而无礼,那么力的无目的性或缺乏规范的使用往往与事先期望达到的效果相差甚远,于是会出现“急而无功”。所以,直当以礼行之。我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些咬文嚼字,有些片面地企图从字面意思上加以突破。姑且做为一种尝试吧。对于接口或“礼”,我认为它是必须的,但是它具体该如何定义,和哪些因素相关,还有待今后研究。
。《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葸,音洗。畏惧貌),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偷,朱紫阳注释为薄也)。”朱子曰:“绞,急切也。无礼则无节文,故有四者之弊。”我觉得这个“绞”字用得好,所谓“欲速则不达”即如此。另外“笃于亲”的“亲”,我认为做《大学》开篇中“亲民”之“新”,意为君子之责任。张子曰:“人道知所先后,则恭不劳,慎不葸,勇不乱,直不绞,民化而德厚矣。”张子,名张载,北宋年间著名理学家,字横渠,关学的开创者,北宋五子之一(其余四人为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后朱熹在此名单上加上司马光,成为道学六先生)。张横渠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认为读书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代表作是《正蒙》。现今社会有很多人喜欢自诩为“直”,口头禅中总有一句“我这个人很直的”,然后不顾场合地点“畅所欲言”,只管自己说得是否过瘾,没有考虑他人的感受或接受程度。我比较认同范祖禹对礼的定义“事有其序谓之礼”,“事有其序”这句话包含了“有”和“序”。先得存在“序”,才能被“有”。“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是表现形式不同的,但是“序”有隐含包括着对象的存在,只有两者或两者以上的对象才能存在“序”,也只有它们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才能形成“序”,那么怎样才能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稳定呢?关系取决于两者之间的作用力和接口(受力点)。作用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这和现实万物之间的关系是相符的;但是发力点和受力点组成的接口,必须关注其发送和接受,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两者关系的稳定。力是“直”接存在的,而“接口”则定义了它的作用范围。这个“接口”也就是“礼”,众多的接口形成了一个系统,即广义的“礼仪”规范。假设直而无礼,那么力的无目的性或缺乏规范的使用往往与事先期望达到的效果相差甚远,于是会出现“急而无功”。所以,直当以礼行之。我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些咬文嚼字,有些片面地企图从字面意思上加以突破。姑且做为一种尝试吧。对于接口或“礼”,我认为它是必须的,但是它具体该如何定义,和哪些因素相关,还有待今后研究。
《论语.公冶长》,子曰:“孰谓微生高直 ?或乞醯(醯,音西。醋)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四书集注》解释为, 微生,姓;高,名。鲁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来乞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虽小,害直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圣人观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故以微事断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我认同的“直”在上篇笔记中已经说明,一曰“顺理”,二曰“由衷”。其中“顺理”的重点在于“顺”。微生高“急人之所急”的想法是不错的,但是方式不恰当。在第三方而言,微生高借的不仅只有物件,还有好名声;当他把东西又借给被人,再次博得了好名声。通过“找人借”和“借给人”,他在实物上没有任何损失,可是另外却多了两个好名声。孔程等夫子认为此等“无本的买卖”实为不直,可是数千年来这种做法在民间确屡见不鲜。我认为这并不是无本的买卖。微生高知道有借用人的需求后,然后去搜索能满足需求的信息,这就其“成本”。最后还是能赚得人情,所谓攒积人脉关系为今后所用。“顺理”可以用“急借用人之所急”勉强一言概之,而“由衷”就带有着自私功利的成分了。所以我也不认同微生高的行为为“直”,对今日信息社会的商业方式亦是如此看法。关于微生高,我找到一本好玩的明末小说《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书中的微生高为守佳人之约而“殉情”淹死。此书作为野史,颇为有趣,以后抽空看看。
?或乞醯(醯,音西。醋)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四书集注》解释为, 微生,姓;高,名。鲁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来乞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虽小,害直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圣人观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故以微事断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我认同的“直”在上篇笔记中已经说明,一曰“顺理”,二曰“由衷”。其中“顺理”的重点在于“顺”。微生高“急人之所急”的想法是不错的,但是方式不恰当。在第三方而言,微生高借的不仅只有物件,还有好名声;当他把东西又借给被人,再次博得了好名声。通过“找人借”和“借给人”,他在实物上没有任何损失,可是另外却多了两个好名声。孔程等夫子认为此等“无本的买卖”实为不直,可是数千年来这种做法在民间确屡见不鲜。我认为这并不是无本的买卖。微生高知道有借用人的需求后,然后去搜索能满足需求的信息,这就其“成本”。最后还是能赚得人情,所谓攒积人脉关系为今后所用。“顺理”可以用“急借用人之所急”勉强一言概之,而“由衷”就带有着自私功利的成分了。所以我也不认同微生高的行为为“直”,对今日信息社会的商业方式亦是如此看法。关于微生高,我找到一本好玩的明末小说《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书中的微生高为守佳人之约而“殉情”淹死。此书作为野史,颇为有趣,以后抽空看看。
冯氏曰:“直者内忖诸己者也(忖,音村,三声,思量),曲者外揣于人者也。家自无醯,则谢之可矣。今惟恐人之不乐我之谢,而必欲给其求,是不能内忖诸己,而己不免揣人意向为转移,究其极为巧言令色,故不得为直。”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恭,又作足共,过度谦敬,以取媚于人。谢氏曰:“二者之可耻,有甚于穿窬也(窬,音于,从墙上爬过去,又如穿窬之贼。)。左丘明耻之,其所养可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盖‘窃比老彭’之意(老彭,商之贤大夫),又以深戒学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我认为,此二者皆违背言之“由衷”原则,故不为“直”。
《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朱子曰:“一乡之人,宜有公论矣,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其有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冯氏曰:“夫至乡人皆恶之,是必不近人情之人也。然至乡人皆好人,此难免专务人人而悦之,为乡愿之徒,亦虚伪无可取矣。”如果好人恶人都喜欢一个人,那么该号人物需要在不同的时候把持不同的善恶观点的,也就是朱子说的“苟合之行”;如果好人恶人都不喜欢他,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人确实无任何可取之处了。孔子认为这两者都不如做一个让好人喜欢而让坏人讨厌的人。处事分明,率直而行。
 ,假定人本有完全的良知,假定“满街都是圣人”,故以为人只须顺其良知而行,即万不致误。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我知之甚少,不清楚这两位思想家假定“性本善”的依据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满街都是圣人”是缺乏客观性的。普通人和圣人的欲求必定是有差异的,况且什么是“良知”这点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的定义也是不尽相同的。隐约觉得陆王心血可能与释禅之道有所联系,此点需要待以后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后再做深入分析和评判。冯氏继续讲到,孔子初无此意。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本不必即可顺之而行而无不通(此句比较绕口,我理解为人之真性情流露,并不是顺之就能行得通的)。故孔子重视“克己复礼为仁”。然礼犹外部之规范。除此外部规范外,吾人内部尚且有可为行为之标准者。若“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吾人之性情之流露,自合乎适当的分际。故“直”尚有行不通处,而“仁”则无行不通处。故仁为孔子“一贯”之道,中心之学说。我在想“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始思想动机是什么,因为从冯氏的观点来看,更像是为了“行得通”。那么“行得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有自私自利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如果仅停止在能“无行不通处”的层面,而不去想上面的问题,那就可能只重视了外在的形式,而忽略或放弃了其本质。我和冯先生在此观点有所分歧,我认为孔子提倡行“仁”,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激发人们进一步去了解和探索宇宙的真谛。天下之事,从无某种定论可以行通或行不通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并且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发展上上世纪,还不是被西洋的坚船利炮给轰开了国门。当然这里面有无数的其他历史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日趋保守和个人功利的儒家思想是最主要的几个原因之一。
,假定人本有完全的良知,假定“满街都是圣人”,故以为人只须顺其良知而行,即万不致误。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我知之甚少,不清楚这两位思想家假定“性本善”的依据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满街都是圣人”是缺乏客观性的。普通人和圣人的欲求必定是有差异的,况且什么是“良知”这点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的定义也是不尽相同的。隐约觉得陆王心血可能与释禅之道有所联系,此点需要待以后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后再做深入分析和评判。冯氏继续讲到,孔子初无此意。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本不必即可顺之而行而无不通(此句比较绕口,我理解为人之真性情流露,并不是顺之就能行得通的)。故孔子重视“克己复礼为仁”。然礼犹外部之规范。除此外部规范外,吾人内部尚且有可为行为之标准者。若“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吾人之性情之流露,自合乎适当的分际。故“直”尚有行不通处,而“仁”则无行不通处。故仁为孔子“一贯”之道,中心之学说。我在想“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始思想动机是什么,因为从冯氏的观点来看,更像是为了“行得通”。那么“行得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有自私自利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如果仅停止在能“无行不通处”的层面,而不去想上面的问题,那就可能只重视了外在的形式,而忽略或放弃了其本质。我和冯先生在此观点有所分歧,我认为孔子提倡行“仁”,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激发人们进一步去了解和探索宇宙的真谛。天下之事,从无某种定论可以行通或行不通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并且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发展上上世纪,还不是被西洋的坚船利炮给轰开了国门。当然这里面有无数的其他历史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日趋保守和个人功利的儒家思想是最主要的几个原因之一。